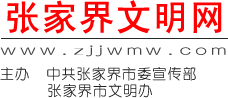陆玄同:治农村婚丧陋习,要软约束不要硬规定
-
“把老人安稳送走、看孩子顺利结婚”,这是很多农户穷其一生的追求,然而,一些地方的婚丧陋习,却让不少农村家庭陷入困局。
据《半月谈》日前报道,在邯郸市的一些农村,村里的男青年结婚,彩礼钱得20万元左右,有的甚至更多。除了彩礼之外,其他开支名目众多,例如“三金”、见面费、赶集费、媒人费等,合计约5万~13万。以广平县南韩村乡南张村为例,办一桩婚事的花费在50万元左右,是10年前的7倍。为了遏止陋习旧俗,邯郸市出台了专门的实施方案,推出移风易俗工作举措,选取6个工作基础较好的县(区)作为试点先行先试,向婚丧陋习宣战。
从举办声势浩大的集体婚礼,到抵制高价彩礼巡回演讲;从规范完善农村红白理事会,到细化婚丧喜庆事宜规则,一年来取得了些许成效,但仍路漫漫其修远。
这不是一地一村的个例,而是全国普遍存在的现象。虽然官方一再强调抵制,各地也出台了相应的规章制度,但收效甚微。几千年的传统在世俗功利的环境下发生的变异,不是一纸规定就能够扭转的。这注定是一场持久战,唯有依靠广泛的宣传和引导,才能逐渐疏松这一板结的“土壤”。
当然这种陋习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。以男权为主的传统社会,女方出阁到男方,是要替男方家里生儿育女,传宗接代,同样男方要通过“下聘”来实现某种“交换”,这就是彩礼的缘由。从儒家思想占据中国文化统治地位,到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覆灭,再到新时代,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但婚丧习俗的传统从未改变,反而随着经济条件的攀升“与时俱进”。
我们看,在改革开放前,虽然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低下,但对于彩礼的要求并不低,最为人所熟知的莫过于“三大件儿”。比如70年代的“手表,自行车,缝纫机”;80年代的“冰箱,电视,洗衣机”,显然,这种聘礼超出了绝大多数家庭能够承受的范围。唯一不同的是,物资虽寡但均,大多数家庭面对的境遇是相等的,加之女方家又严守“姑娘到了年龄一定要嫁”,双方多了协商的渠道。
及至改革开放后,不同经历或背景的青壮年,走上了不同的道路,或读书、或创业、或经商、或继续务农。等到新世纪后,贫富差距不断拉大,务农的那部分人面朝黄土背朝天,面对孩子结婚的问题必然就水涨船高,这时候稍微富裕一点的女方要多少就给多少,但家庭一般的就会被边缘化,丧失了在彩礼上的“竞争权”。但谁又忍心自己的孩子讨不到媳妇,只能被东借西凑裹挟着跑。
而丧葬亦是如此,“死者为大”的传统观念下,“风风光光”下葬历来都是光宗耀祖的事,尤其是在物质生活较为充裕的当下,风光大办就意味着一洗往日的贫穷与落后,锣鼓喧天的背后更像是一种对曾经不堪的诀别。思想的贫瘠使很多家庭唯有通过金钱的巨大消耗,才能彰显逝去人的价值,以及家庭在当地的社会地位。
所以农村业已形成的这种陋习,有着其根深蒂固的思想根源,不是行政力量介入就可以解决的。万不可操之过急,一旦强硬的制度和传统观念碰撞,会使问题的解决走向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,要么顺利解决,要么引发更大的冲突。
没有人愿意在这种陋习盛行的漩涡里挣扎,但似乎谁都挣不脱。如果有人愿意当这一股清流,会很快被同村人的口水淹没,甚至可能被孤立。
以社会层面来说,这无疑是一种陋习,引发的攀比效应加大了部分贫困家庭的支出成本。但话说回来,这也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,民众有这样的权利。
对于政府来说,唯有多引导,多宣传,以年轻的家庭为切入点,不断进行文明婚丧意识的灌输,使之有一定的传播土壤,才能以相应的柔性制度进行约束,继而成立相应的机构对全村的婚丧嫁娶事宜进行统一筹划。但有一点需要明确,不管何种制度都是要寻找共性需求,满足个性表达,不可千篇一律,也不能整齐划一。(文/陆玄同)